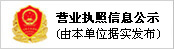故乡·老井·酒
新闻分类:墨香酒韵 来源:古贝春报编辑部 发布日期:2014-04-01
华北地区是缺水的,但家乡那方慈爱的大地却馈赠给当地一个水晶般的礼物,仿佛在故乡的每一寸土地上随意地凿一个口子就能冒出甘甜的水来。老辈人讲:在这地下有龙掌握泉眼,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对于此类美好传说,我是信以为真的,因为在邻近的村庄,就很难打出甘甜的水来,我是暗自庆幸有龙潜于我们村的地下,赠予这绵延不绝的水源的。记忆中的村子里,仿佛到处都有形态各异的水井,井床上终年浸渍着水珠,每逢夏日,苍翠的青苔便布满整个井壁。
如今住进了楼房,清泉从水龙头汩汩地流出,它们的形态依旧是那般的温润和剔透,但却分明少了原有的灵动,夹杂更多的是人世间的浮华和焦躁。而我梦中的老井,早已跟整个故乡一样掩埋于那层浅浅的黄土之下了。当再有月亮升起,如霜的月光也再难呈现《静夜思》中的意境了。
井,故乡,便是一脉清泉把一份乡愁灌输进每个人的心底,把家乡所有的印记清晰地刻在它哺育的每个人心间。
故乡的井从不遵循艺术而堆砌,它不是诗,更难像画。井壁用青砖堆砌,井口用几块青石封口,这便是这些井留给我的印象。都说井伴辘轳,但老家的井上从未有过辘轳,能让我联系到的与井有关的只有扁担和水桶,还有担水的父亲。每天早晨,父亲担水的声音总会把我从睡梦中惊醒,先是铁皮水桶在扁担上悠闲地荡着发出吱吱扭扭的声响,不大一会儿,便听到这声响分明急促厚重起来,最后便是桶中水撞击水缸发出的轰鸣。孩子们依次起床了,我能看到院内那口大缸氤氲散发出的水汽,还有那和着晨光荡漾的光泽。我有时候会跟在父亲身后去担水,父亲会双腿跨过井口,把水桶用带绳的钩子钩住,水桶会碰撞井壁发出叮当叮当的声响,也能隐约听到水咕咚咕咚灌进桶内的声音。父亲双手抓住绳子,往上提水时,会尽量地把身子弯下,年轻的父亲胳膊上会爆起突兀的青筋,仿佛有用不完的力气。父亲担水时,扁担杂耍般地在他肩头上下跳动,他会腾出两只手来,熟练地从兜里掏出烟叶儿,熟练地卷好一颗旱烟点上。父亲熟悉这老井,老井更见证了父亲成长的辛酸。1964年挨饿,12岁的父亲倚靠着井床,体会过死亡,仿佛一阵风就能把他柔弱的生命带走,但他挺过来了。14岁那年祖父去世,父亲便开始给全家担水,被这井床的石头磕破过膝盖,扭伤过脚腕。16岁,父亲便是在这老井边接过祖母准备的行囊,只身踏上去东北谋生的道路。1990年,村里改成自来水,父亲再也不用担水了,扁担歇了,老井因无人疏导淤塞成了一口枯井。
就是这口井让我对其怀有别样的情感,邻居老嫂子至今还会讲那段往事,小时候姐弟几个趴到井床上,把头深深地埋到井里,在那井内的水面上,依稀能看到姐弟几个快乐的样子。恰好邻居老嫂子经过,看到这种情形吓傻了。“该先按住那个呢?”老嫂子说:
“按住那个男孩儿,丫头掉下去就掉下去吧。”这是她的选择。
“为什么呢?”姐弟几个问她。
“你家丫头多,就这么一个儿子。”老嫂子笑得那般夸张。
可那次以后,我还是不小心掉进了这口井里,头上至今还有一块伤疤。一帮孩子玩耍,我朝后倒了几步,只感觉眼前一晃,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模糊听到井口有人喊我的名字,稀里糊涂地便把绳套压在了胳膊下……
闻讯赶来的祖母扶着我走了好久,我才哭出声来,祖母用毛巾按着我头上的伤口,心疼地只掉泪。
幸亏那井已枯了,不然我可能就淹死了。
事后,祖母跪在井旁烧了很多纸钱,父亲和邻居们把闲置的一个大碾盘盖到井口上,老井睡了。但我头上的伤疤却让我永远忘不了这口老井,但我并不恨它,就跟父亲一样,只是这份记忆在我的头上,却在父亲和乡亲们的心里。
故乡离公司直线距离不足千米,我是闻着古贝春酒的清香长大的。酿好酒需有好水,仿佛是同一条蜿蜒的地下清泉源于古运河底,叮咚作响漫向故乡大地,哺育了我一辈一辈勤劳朴实的乡亲,酿造了这盈盈欲滴的甘洌琼浆。擎一杯古贝春酒,便似家乡那老井中荡漾的清泉,倒映着故乡的蓝天白云,阡陌斜阳。氤氲散开的酒香,便似井旁如霜的月光,把一份相思勾起,把一份思乡灌满。噙一口古贝春酒,蕴含几分故乡水的滋味,能藏多少五谷的清香,能翻出几多往事。有苦涩中带有温馨的,有苦难中蕴含幸福的。就如父亲好酒,足可在醉眼朦胧间回味一生的艰辛苦楚,幸福和快乐。而我或将用一生探索这家乡水的深邃魅力,探索这家乡古贝春酒蕴含的每一份情感和感动。
还记得小时候趴在井口俯看井水的感觉,在荡漾的水光里,有我快乐的脸庞,在那静得足能听到呼吸、心跳的老井中,能清晰感觉到扑向面庞的清凉,这清凉中混杂着水的味道,泥土的清香,还有其尘封的往事和一生的慈爱与宽容。
哦,故乡,老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