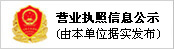宇宙和青苔
新闻分类:墨香酒韵 来源:行管办 朱珏 发布日期:2024-12-06
办公楼前的柿子树打起灯笼的时候,秋天就到了。卫生区的落叶由绿变黄,由少变多,从这头扫到那头,黄橙绿色跟着扫帚尖跑来跑去,笔刷似的。
太阳直射点从夏至开始南移,在它到达南回归线之前,白天会持续变短。地球遵循着公转和自转的规律,作为宇宙里一颗微小的尘埃,带着谨遵农时的人们和循时迁徙的候鸟,漫无目的地漂流。
秋天不是突然跳出来的,秋天是踩着一场又一场的雨,用凉爽,用湿润,用越飘越高的云,用氤氲模糊的雾气,一步步地走近,等到人在连日的潮湿里感叹冬日将至的时候,秋天再拨开层层云雾,赶在立冬前再给一个晴天。
而树叶不管晴雨,秋天总是在掉。高大的落叶乔木伫立在卫生区的两侧,春天掉球,秋天落叶,不定期褪几块树皮。阳光从树的枝丫间穿过雾气,显出丝丝缕缕的形状,倾泻下来,有飞虫藏在将落未落的树皮里,时不时飞出来捍卫一下它小小的领地。阴雨连绵的时候,鸟雀的叫声也见少,法桐无声地接着冷雨的润泽,无声地落下枝叶,连带着冬青和潮湿的泥土,随着宇宙里尘埃一样的星球一起沉默。
沉默似乎是生命的常态。大音希声,万物在沉默中生长,也在沉默中消亡。
曾经有一段时间,逻辑推理和智商测试在网络上风靡,随之被关注到的还有一些哲学和逻辑上的思辨,诸如“只为那些不给自己理发的人理发”的理发师悖论、“人不能穿越回自己祖父的婴儿时期并杀死他”的祖父悖论,还有“缸中大脑”的理论,它虚构了一个把人的大脑取出,给予能量和电信号刺激从而让大脑产生各种感觉,并以此为研究的邪恶科学家。被实验的大脑终其一生都无法知道自己生活在“楚门的世界”,直到大脑衰老、萎缩,它都看不到真实的天空、草地和那个邪恶的科学家本人。
很阴暗的理论,但它确实引出了什么东西。它给我最深的感触是一个印证——人类果然在无论任何时候,都没有放弃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关于“我”是什么的问题。即使现实世界是那么引人注目,食物的香气、冷热交替的气候、声色犬马、口腹之欲……即使需要面对的、等着体验的有那么多,人总能在某个时刻突然被触动,问出那几个幽灵一样久久困扰着整个人类群体的问题——我是谁,从何处来,到何处去。
这样的句式很容易让人想到那句经典回答——“贫僧唐三藏,从东土大唐而来,要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然而与拿着通关文牒一路借宿的唐僧不同,对我们来说,从来没有一个确定的目的地能给予我们解答一切的经书。于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人们开始产生信仰,相信天庭地府、天堂地狱,相信轮回天道、神爱世人,发展到现在,更多人选择信仰科学。
科学也算一种信仰吗?算的。物理和化学让我们更加直观地看清这个世界,也让我们更加相信数据能够表达一切。直到现在,我们都在幻想有着强大科技的、无所不知的外星人来到地球,侵略或者探索。著名科幻小说《三体》是这样,电影《宇宙探索编辑部》中也刻画出了这样一个典型的、木讷的、行为略显古怪的科幻爱好者。影片里那个颓废落魄、又固执地追寻外星人的科幻杂志主编唐志军,用极其“不严谨、不科学”的方式找到能与外星人联系的方式之后,迷茫又充满希冀地想让对方为自己解答:“我们人类,存在在这个宇宙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我看这部电影时正值秋雨连绵,卫生区积雨路上的树叶不那么容易打扫,下水道口恰到好处地高出地面一点,让叶子有了化身为舟的契机。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把小舟们从水里推出来,再把水推到下水道口,好让地面也干得快些。当我拿着扫帚挑起一片带土的青苔的时候,突然意识到自己竟然在回想这个问题。
“意义”从来都是很难回答的问题,“存在的意义”尤甚,因为它非常主观。就像我认为扫帚存在的意义是帮助我快速地清洁厂区里的落叶,但地面上的混凝土可能会觉得“那就是个痒痒挠”,或者那片刚刚因为被我误伤而失去了生存环境的青苔,它大概会觉得扫帚存在的意义是谋杀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一片青苔。
如果拿这个问题去采访,会得到的答案大概分为以下几种。一是反问型,比如:“存在的意义?没意义那不活了?”一是现实型,比如:“与其想这个不如多想想晚上吃什么,净想那没用的。”一是感悟型,比如:“存在的意义就是体验人生的过程。”再比如精神病型:“不如去码头整点薯条。”
如何努力地过好生活这个命题已经占据了我们普通人的绝大部分生命,留给我们和星辰大海的时间或许只有偶尔抬头的那一眼。看到、疑惑、发问、结束。这个过程快得不可思议,毕竟时间不等人,我只是顺手多扫了一片青苔进落叶堆里,同伴的扫帚就已经“挠”到前面那段路上了。我加快进度把落叶收成一堆,正准备赶上他们,却发现抬眼又是一块青苔。
秋冬是一片肃杀,秋冬的阴雨更是一片灰白。那片青苔却这样从灰色里孕育出来,用深浅不一的绿色填补着砖缝,与凋零的落叶格格不入地绽放着,固执地、渺小地、脆弱却又生生不息地绽放着。
这是比起地球,比起人类都要渺小太多的存在,世界上给它的容身之所并不多,它需要潮湿、需要略高的温度、需要永不直射的太阳;它没有深深的根系,只能开出像米一样小小的花。它不能像法桐和冬青一样度过冬天,但每年这个时候,我都能见到它。
现实中的理想主义者估计比青苔还要少,生存空间也更加苛刻。他们无法不固执地追寻自己的理想,像唐志军那样,冒着被骗的风险、被嘲笑的声音,走千万里路,去寻找一个自己都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真相”。
但当你问他们是否值得,他们大概会说出那个像青苔一样的答案——“朝闻道,夕死可矣。”
太阳直射点从夏至开始南移,在它到达南回归线之前,白天会持续变短。地球遵循着公转和自转的规律,作为宇宙里一颗微小的尘埃,带着谨遵农时的人们和循时迁徙的候鸟,漫无目的地漂流。
秋天不是突然跳出来的,秋天是踩着一场又一场的雨,用凉爽,用湿润,用越飘越高的云,用氤氲模糊的雾气,一步步地走近,等到人在连日的潮湿里感叹冬日将至的时候,秋天再拨开层层云雾,赶在立冬前再给一个晴天。
而树叶不管晴雨,秋天总是在掉。高大的落叶乔木伫立在卫生区的两侧,春天掉球,秋天落叶,不定期褪几块树皮。阳光从树的枝丫间穿过雾气,显出丝丝缕缕的形状,倾泻下来,有飞虫藏在将落未落的树皮里,时不时飞出来捍卫一下它小小的领地。阴雨连绵的时候,鸟雀的叫声也见少,法桐无声地接着冷雨的润泽,无声地落下枝叶,连带着冬青和潮湿的泥土,随着宇宙里尘埃一样的星球一起沉默。
沉默似乎是生命的常态。大音希声,万物在沉默中生长,也在沉默中消亡。
曾经有一段时间,逻辑推理和智商测试在网络上风靡,随之被关注到的还有一些哲学和逻辑上的思辨,诸如“只为那些不给自己理发的人理发”的理发师悖论、“人不能穿越回自己祖父的婴儿时期并杀死他”的祖父悖论,还有“缸中大脑”的理论,它虚构了一个把人的大脑取出,给予能量和电信号刺激从而让大脑产生各种感觉,并以此为研究的邪恶科学家。被实验的大脑终其一生都无法知道自己生活在“楚门的世界”,直到大脑衰老、萎缩,它都看不到真实的天空、草地和那个邪恶的科学家本人。
很阴暗的理论,但它确实引出了什么东西。它给我最深的感触是一个印证——人类果然在无论任何时候,都没有放弃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关于“我”是什么的问题。即使现实世界是那么引人注目,食物的香气、冷热交替的气候、声色犬马、口腹之欲……即使需要面对的、等着体验的有那么多,人总能在某个时刻突然被触动,问出那几个幽灵一样久久困扰着整个人类群体的问题——我是谁,从何处来,到何处去。
这样的句式很容易让人想到那句经典回答——“贫僧唐三藏,从东土大唐而来,要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然而与拿着通关文牒一路借宿的唐僧不同,对我们来说,从来没有一个确定的目的地能给予我们解答一切的经书。于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人们开始产生信仰,相信天庭地府、天堂地狱,相信轮回天道、神爱世人,发展到现在,更多人选择信仰科学。
科学也算一种信仰吗?算的。物理和化学让我们更加直观地看清这个世界,也让我们更加相信数据能够表达一切。直到现在,我们都在幻想有着强大科技的、无所不知的外星人来到地球,侵略或者探索。著名科幻小说《三体》是这样,电影《宇宙探索编辑部》中也刻画出了这样一个典型的、木讷的、行为略显古怪的科幻爱好者。影片里那个颓废落魄、又固执地追寻外星人的科幻杂志主编唐志军,用极其“不严谨、不科学”的方式找到能与外星人联系的方式之后,迷茫又充满希冀地想让对方为自己解答:“我们人类,存在在这个宇宙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我看这部电影时正值秋雨连绵,卫生区积雨路上的树叶不那么容易打扫,下水道口恰到好处地高出地面一点,让叶子有了化身为舟的契机。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把小舟们从水里推出来,再把水推到下水道口,好让地面也干得快些。当我拿着扫帚挑起一片带土的青苔的时候,突然意识到自己竟然在回想这个问题。
“意义”从来都是很难回答的问题,“存在的意义”尤甚,因为它非常主观。就像我认为扫帚存在的意义是帮助我快速地清洁厂区里的落叶,但地面上的混凝土可能会觉得“那就是个痒痒挠”,或者那片刚刚因为被我误伤而失去了生存环境的青苔,它大概会觉得扫帚存在的意义是谋杀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一片青苔。
如果拿这个问题去采访,会得到的答案大概分为以下几种。一是反问型,比如:“存在的意义?没意义那不活了?”一是现实型,比如:“与其想这个不如多想想晚上吃什么,净想那没用的。”一是感悟型,比如:“存在的意义就是体验人生的过程。”再比如精神病型:“不如去码头整点薯条。”
如何努力地过好生活这个命题已经占据了我们普通人的绝大部分生命,留给我们和星辰大海的时间或许只有偶尔抬头的那一眼。看到、疑惑、发问、结束。这个过程快得不可思议,毕竟时间不等人,我只是顺手多扫了一片青苔进落叶堆里,同伴的扫帚就已经“挠”到前面那段路上了。我加快进度把落叶收成一堆,正准备赶上他们,却发现抬眼又是一块青苔。
秋冬是一片肃杀,秋冬的阴雨更是一片灰白。那片青苔却这样从灰色里孕育出来,用深浅不一的绿色填补着砖缝,与凋零的落叶格格不入地绽放着,固执地、渺小地、脆弱却又生生不息地绽放着。
这是比起地球,比起人类都要渺小太多的存在,世界上给它的容身之所并不多,它需要潮湿、需要略高的温度、需要永不直射的太阳;它没有深深的根系,只能开出像米一样小小的花。它不能像法桐和冬青一样度过冬天,但每年这个时候,我都能见到它。
现实中的理想主义者估计比青苔还要少,生存空间也更加苛刻。他们无法不固执地追寻自己的理想,像唐志军那样,冒着被骗的风险、被嘲笑的声音,走千万里路,去寻找一个自己都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真相”。
但当你问他们是否值得,他们大概会说出那个像青苔一样的答案——“朝闻道,夕死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