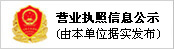春节“三味”
新闻分类:墨香酒韵 来源:古贝春报编辑部 发布日期:2011-01-27
“瑞雪飘飘降吉祥,吹吹打打拜花堂。除夕之夜巧妆扮,欢欢喜喜看新娘……”。这首由童声齐唱的歌曲,一晃十几年过去了,但那清脆悦耳的旋律至今仍在耳旁回荡。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一次春节联欢晚会上,一群身着中国传统服装的孩子们,用纯净的声音赢得了阵阵掌声,在那个白雪飘飞的除夕之夜,把春节崭新的气息送到了万户千家,此时神州大地一片沸腾。
当这祥和的节日又要悄悄走来的时候,我总在内心品味这春节的滋味,尽管这滋味已历时千载,但在岁月的沉淀中,在情感的交织下却愈发地香浓了。
鞭炮
父亲的左臂上有条长长的疤痕,是鞭炮的灼伤,那疤痕青筋暴起,很是恐怖。按说父亲应该对这鞭炮痛恨至极,起码也总该有种“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畏惧感吧。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父亲非但没有因这疤痕而有所收敛,反而会“变本加厉”买更多鞭炮。尽管母亲对他这种浪费钱财的行为有所抱怨,但也并没有真正地阻止过什么。父亲买了这些东西后,会极力怂恿我的弟弟去放。他会支起耳朵,眯着眼睛,听那鞭炮清脆的声响,看那鞭炮直冲云霄,炸开的烟雾弥散开来。若那响声不是很好,明年这鞭炮的个头定会再次增大,买鞭炮的花销也会随之增加。
我的父亲是节俭的,平日很少花钱为自己置办点什么,惟独对这鞭炮却很舍得花钱。我对父亲的这种行为很不理解,这鞭炮之于父亲,之于春节到底意味着什么?
父亲生于50年代,挨过饿,受过很多苦,有着我们这代人无法体味的辛酸童年。父亲8岁那年春节,跟村里其他孩子一样,早早地把一根长竹杆放到了家族“管事儿”那儿,为得是让他给自己的竹杆上挂上一串鞭炮,以便在初二的早上燃放。在当时艰难的生活条件下,鞭炮对于男孩子来说是一件多么珍贵的东西呀!一个大家族用凑来的有限的钱财,买回极其有限的鞭炮。家族“管事儿”由于各种原因,没给父亲的杆子上挂上鞭炮。等到初二早上,父亲兴奋地的去取竹杆时,发现上面并没有鞭炮,便气愤地去找“管事儿”理论。可是谁会把一个几岁的孩子放在眼里,父亲被三两下推出屋去。看着其他男孩子竹杆上噼啪作响的鞭炮,父亲委屈得直掉眼泪,可怜兮兮地的跟在其它人后面,疯抢未炸响的鞭炮。当父亲把一个以为未响的鞭炮抢到手后,生怕其它孩子来抢,就把它塞到棉袄袖里。谁知那鞭炮却在父亲的袖子里炸响了,袖子被炸得粉碎,破败的棉絮,血肉模糊的左臂,给我父亲本就不幸的童年,平添了一段更为刻骨铭心的记忆。
我能体会8岁的父亲所承受的肉体上的痛苦折磨,也更能体会今天父亲对鞭炮的特殊情感。因为,在父亲的内心最深处有个情感的空缺,一种未得到满足的缺憾。同我的父亲一样,时代决定那代人所拥有的遗憾实在太多太多。他们似乎要弥补这些缺憾,却发现很多东西根本就无法挽回。于是他们会用加倍的情感附加到自己的孩子身上,为的是别再让自己的孩子有遗憾,这也许便是父亲对鞭炮特殊情感的渊源吧!
鞭炮的起源无需再去长篇累牍,但鞭炮作为一个春节的重要符号却早已在中国百姓心中根深蒂固。这震天的响声,是对逝去岁月的一种深沉怀念,是对来年诸事平安的一种热切祝愿。它传达着中国百姓对新春的渴盼,传达着一份份深切的祝福,期盼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爆竹声声辞旧岁,岁岁平安岁岁福。我留恋这声声鞭炮,更祝愿所有的老人春节快乐!
拜年
中国百姓的性格是含蓄的,这种性格反映在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尤其在情感的表达上,无论是长辈与晚辈之间、夫妻之间还是朋友之间,情感的交流不会轻易地表现在言语上,而更多的是通过一种行动来表达。比如:拜年。
如今,短信拜年、电话拜年已是司空见惯,并大有替代传统跪拜式拜年的趋势。跪拜式拜年的由来早已无证可考,但能够明确的是,他是晚辈对已故祖先以及健在长辈所传达的一种新年的祝福,是一种情感的肢体语言表达。这种拜年方式虽然已经延续了很长时间,但在家乡农村每年春节这仍是一种不可缺少的活动。
丈夫生活在一个很大的家族里,家族中光同辈的哥哥就二十几个。小时候,他跟在那些大哥的身后,挨家挨户地去磕头拜年。他当时并不明白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只是跟在身后图一乐,年长的大哥怎么做,他就照着做。但每到一家,他倒也收获颇丰,长辈们会追出门来,把糖果塞满他的口袋,摸摸脑袋夸奖一番。
一年一年春节的更迭中,丈夫长大了,但可拜年的老人却越来越少了。能吃上当年初一的饺子,收上几个晚辈们的跪拜,对于他们来说,等于又熬过了一年。在晚辈们呼呼啦啦的跪拜声中,他们得到的仿佛也是一种儿孙满堂的满足。
结婚后第一年的初一早上,丈夫兄弟两个带着我给公公婆婆磕头拜年的时候,婆婆一手拉住我,示意我算了吧。我没有依着婆婆,深深地跪了下去,旁边的兄弟两个也深深地俯下身去。不知道为什么?我的鼻子老是酸酸的,此情此景极是伤感。一个跪拜,丈夫哥俩所能表达的情感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应该是一份难以言尽的感恩吧。丈夫姊妹几个真真的长大了,但在哥俩年年的跪拜中,公公、婆婆也的确老了,老的那般突然。
初一凌晨,依旧有绵延不断的鞭炮声响,整个神州大地在苍茫的夜色中互道着春节的祝福。依旧是丈夫哥俩儿带着我,去跟同族的长辈们拜年。每到一家,长辈们总会拽住我,不让我跪下,推说怕弄脏我的衣服,拉着我嘘寒问暖。那兄弟两个却把那头磕得嘭嘭响,这时长辈们非但不阻拦他们,甚至还嗔怪道:“你这俩傻小子,一年了也不回家看看!都快不认识你们了,磕吧!磕吧!”此时的哥俩或有愧疚,或也有自己的无奈吧。但长辈们会笑笑抓住哥俩的手,欢喜得掉下泪来。长辈们总会给我历数丈夫小时候的种种“罪行”,那年砸了二爷的玻璃、那年点了三爷的柴垛等等。这时候,总会引来那样难得的开怀大笑,尽管丈夫哥俩不常回家,但老人们都还惦记着他们,或许更希望年轻人也不要忘记他们吧。
那年初一,仅仅几家,我们却转了好长时间。每到一家,我们都会坐下来,跟老人们说说话。老人们也总那样真诚地嘱咐我们,好好工作,注意身体,没事常回家看看。
当丈夫告诉我哪个长辈去世的时候,眼前总能浮现出他们慈祥的面庞,心里自然一阵落寞。这春节呀,它所存在的意义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肤浅,它更像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种亲情的交流与宣泄的机会。我从不把春节的种种仪式归结为迷信,那是祖先对美好事物向往所寄予的一种心灵暗示,把其通过一种活动表达出来,其所表达的是礼、孝、仁、义的优良传统。我们大可没有必要抬高自己高傲的头颅,不屑于这所谓的迷信。在这难得团聚的节日里,我们遂了老人的美好愿望,何尝不是一种感恩呢。若也真以为跪拜式拜年是一种低人一等下作的举动,那我们的中国年也许就真在纸醉金迷的当今社会,慢慢蜕变成一种可有可无的节日罢了。
古贝春
从温暖如春的楼房回到寒风料峭的农村老家,最难熬的便是这恼人的寒冷。尽管穿得很厚,回到家后依旧会冻得缩手缩脚。但每年回到老家,年的氛围却浓重起来,让人在寒冷中能体会到春节的火热和浓得化不开的情感纠葛。
这时候的乡村上空,总是不时传来零星的鞭炮声响,家家户户沉浸在祥和的节日氛围中,仿佛平时冷寂的乡村,一下就涌进了很多人来,整个村庄也仿佛热闹沸腾起来。
在这淳朴宁静的小村里,在家家欢庆的热闹背景下,总会有熟悉的东西映入我的眼帘。是的,是我们公司那盏盏火红的灯笼,还有那张张吉庆的古贝春春联,在乡村料峭的寒风中,那样浓艳地烘托着节日的气氛。我喜欢大门下悬挂的随风摆动的大红灯笼,那飞舞的姿态向路人表达着团圆美满的幸福内涵,其浓重的中国红便是当今这红红的中国年特有的色彩。
古贝春早已不再是当初那个“陌生人”,需要煞费苦心方能走近这里。他更像是自家的一个孩子,那样顺理成章地走进了万户千家,他也无需再介绍自己,因为他早已融入了寻常百姓的生活。
年夜饭,觥筹交错中的古贝春酒,是一曲荡气回肠的《乡恋》,家人或是朋友离别一年,共叙相思之情。离家时,寂然无声的古贝春酒是一首《儿行千里》,寄托了父母对即将回城工作的儿女们无尽的真挚情感。是古贝春酒,让这春节变得像是婉约的诗歌,在这深情脉脉的浓重氛围中,一切变得柔和而温情。
到初五的早上,我们该收拾东西回城了。我们也要收拾起新年的心情,准备新一年的工作了。这时候的丈夫,仿佛有说不出的伤感。他总是磨磨蹭蹭地拖延时间,一会儿到这边看看,一会去那边瞧瞧。他还会摘下门口悬挂的古贝春灯笼,轻轻掸掉上面的浮沉,用塑料袋小心地包好。我何尝不知道,此次一走,下次再回家乡,恐怕将是另一个春节了。
丈夫那天问我,是否记得古贝春很早的时候曾在春节期间发行过一张类似年画的宣传画?丈夫一提醒,我记起了那张宣传画的确曾在很多人家张贴过。它是以我们公司的寿星雕塑为基础,经染色处理构成的一幅吉庆的彩色纸画。丈夫说,那是它小时候对古贝春最美好的记忆,长大后,曾经亲自到那寿星雕塑前瞻仰过。那画的宣传语好像是这样写的“国营武城酒厂恭祝大家新年快乐!”。或许在那以前,古贝春就已走进了百家欢乐的新春佳节,但却也是从那时起,古贝春也给这中国年涂上了自己浓浓的颜色。
每年春节联欢晚会结束的时候,总会响起李谷一的那首《难忘今宵》,那曲子的旋律平实委婉,却略带淡淡伤感,歌词虽曾被鄙夷有些矫情,但每年春节,当这旋律伴着此起彼伏的鞭炮声响起的时候,我们何尝不是心怀一种时光流逝的感慨,在无法阻止岁月更迭的遗憾中体味一种淡淡的怀念与忧伤呢!